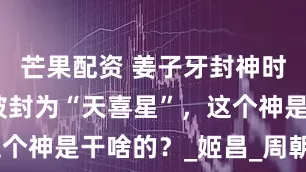文/郭正新荣耀配资


新中国成立前,西藏的交通极为落后。被称为“世界屋脊”的西藏与内地之间雪山重重,江河纵横,不通公路,只有人畜小道和骡马驿道。从青海西宁或四川雅安到拉萨往返一次,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,运输全靠人背畜驮。在大江大河上,只有一些溜索绳、牛皮船和独木舟,仅在个别渡口才有较大的马头平底木船。交通的落后、封闭,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,西藏人民处于极端贫困和沉重压迫之中。
遵照党中央、毛泽东的命令和指示,1950年3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等部队,开始了进军西藏、解放西藏的伟大征程。毛泽东要求“一面进军,一面修路”。这既是保障部队进军的迫切需要,又是着眼西藏长远发展和稳定的战略之举。时任18军参谋长、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司令员的陈明义,率领10万筑路大军,经过4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战,修通了西藏第一条现代公路——川藏公路,结束了西藏不通公路的历史。之后,他又担任工程指挥长或总指挥,带领军民先后修建了西藏第一座机场、第一条国际公路、第一座代航空港。陈明义被人们称为“西藏现代交通事业的开拓者”。
修筑西藏第一条现代公路——川藏公路
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,沿途没有公路,人烟稀少,经济落后,粮食、物资严重匮乏。数万大军在不通公路的千里高原行军作战,衣食住行和作战的各项保障物资,当时估算每人年需量约1000公斤,每头牲口年需量约2500公斤以上。因此,进军西藏的最大困难莫过于补给,而解决补给问题的关键又在于修通进入西藏的公路。
时任西南局、西南军区主要领导的邓小平和贺龙,向中央上报了修建川藏公路的意见,获得批准。这条公路东起成都西至拉萨,包括成都至康定的川康公路,以及康定至拉萨的康藏公路,全长2400余公里。公路穿越整个横断山脉的二郎山、折多山、雀儿山和矮拉、色齐拉、米拉等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险峻大山,横跨岷江、大渡河、金沙江、澜沧江、怒江、尼洋河等众多汹涌湍急的江河,横穿龙门山、青泥洞、澜沧江、通麦等8条大断裂带。施工地域地形复杂,高寒缺氧,天气多变,地层破碎,泥石流、塌方、碎落、雪崩、水毁等严重灾害频发,给筑路工程带来巨大困难。
1950年2月,西南军区成立了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(简称“支司”),统一组织支援进军的后勤保障和公路修筑。18军党委分工陈明义留守后方,率领18军大部兵力,协助支司完成支前运输和筑路等任务。
陈明义是从大别山走出来的老红军,河南省商城县人,1930年参加共青团,1931年参加红军,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开辟鄂豫皖苏区、坚持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和4次反“围剿”作战,经历了长征和西路军西征。抗日战争时期,参加了百团大战,率部参加对石家庄、德州铁路的破袭战斗,领导冀南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军的“铁壁合围”。解放战争时期,参加了开辟豫皖苏解放区和淮海、渡江、赣中、湘南、成都等战役。1949年2月,18军在河南鹿邑县组建,张国华、谭冠三分别担任军长、政委,豫皖苏军区参谋长陈明义被任命为军参谋长。当时,他只有32岁,但早已是久经战火硝烟、艰险环境考验和锻炼的优秀指挥员。
川藏公路成都至雅安段132公里,1925年开始修建,1932年初步通车。雅安以西的公路建设分为两段:从雅安经康定、甘孜至德格县的马尼干戈,国民党政府时期建有约700公里旧道,建设标准极低,年久失修,损毁严重,汽车早就不能通行,需恢复重建;从马尼干戈至拉萨的1572公里,属完全新建工程。
1950年4月13日,筑路工程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。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6个工兵团和18军3个步兵团、军直工兵营、侦察营,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雅甘公路工程处职工、民工的配合下,于1950年8月将公路修至甘孜,年底前又修至马尼干戈。这期间最艰巨的任务是二郎山工程。二郎山是川藏线上的第一座大山隘口,上山45公里,下山45公里,夏季多雾多雨,冬季冰冻雪封。在这里筑路,面对高寒缺氧的困境和地质灾害频发的威胁,更困难的是当时无大型机械,主要靠简易工具,部队给养也难以保障。
靠前指挥,是陈明义的一贯作风。他登上二郎山,环视在此施工的18军162团和158团的战士说:“同志们!在二郎山上筑路,是部队打的第一场硬仗。我们从豫皖苏走来,纵横8省,不知打了多少漂亮仗。今天毛主席命令咱们在青藏高原修一条路,在这个世界最高的筑路战场上,我们一定要再打一个漂亮仗。”陈明义的讲话,激起了阵阵热烈掌声,官兵们喊出了“天大困难像个豆,好马崖前不低头”“天上没路修一条”的誓言,工地上掀起了火热的施工浪潮。
在陈明义和团领导的指挥下,战士们奋战在几十里长的烂泥路上,用铁簸箕挑、小推车运,清理没膝或半人深的淤泥,一天忙下来,人人都穿上了“泥子服”,成了“大花脸”。二郎山乱石满山岗,部队用撬、搬、推、炸等办法降伏“石老虎”,把路面拓开加宽。在陡峭的岩壁上,战士们身绑保险绳,抡锤打炮眼,炸石劈山,凿壁开路。当地阴雨连绵,病虫肆虐,一段时间施工人员患病率高达1/3;官兵每天进行12个小时以上的强体力劳动,夜晚“山坡架帐篷,睡在云雾中”。在艰难困苦面前,大家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热情。1950年8月25日,二郎山路段终于建成粗通。“二呀么二郎山,哪怕你高万丈,解放军,铁打的汉,下决心,坚如钢,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……”这首唱遍全国的《歌唱二郎山》,充分反映了筑路官兵的英雄气概。
1951年1月,西南军区决定支司与18军留驻四川、西康的部队合并,组建18军后方部队司令部(简称“后司”),以加强对筑路和支前运输的统一领导。陈明义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。之后,又建立了康藏公路工程委员会,亦称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,陈明义任司令员,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穰明德兼任政委。18军筑路部队(辖部分工兵团),西南公路工程局第一、第二施工局,加上由四川等地组织的上万名民工和为施工服务的运输队伍等,组成了10万筑路大军,担负从马尼干戈向拉萨方向新建公路的任务。
陈明义出身贫寒,小时候是放牛娃。参加革命后,他在战斗实践中努力学习,文化水平不断提高。面对筑路工程技术这个新课题,他认真阅读专业书籍,虚心向工程技术人员请教,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渐懂得了水文、地质、勘测设计、铺路架桥等技术知识,掌握了在高原特殊条件下施工的规律,加上他长期做参谋工作,具有善于谋划和组织落实的素质,因而对筑路工程实施了强有力的领导。
当年修筑川藏线,毫无地质资料,是以边勘测边施工的方式进行的。1951年,后司派出6支勘测队,勘探昌都至拉萨的线路。勘测队队员们历时一年行程万里,勘察出3条比较线。其中北线所经地段较为平坦,工程量比南线小,但地势高寒,冬季冰雪封山严重;南线所经地段海拔较低,并且多为农业区,森林资源丰富,又靠近边防线,但地质情况复杂,且比北线长200余公里。在定线会议上,走南线还是走北线出现分歧。陈明义明确表示:藏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和西藏边防的巩固,应该是选择线路的立足点。从长远看,走南线对国防巩固和新西藏开发更为有利。随后,他和穰明德政委到重庆向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汇报。走南线的意见得到了贺龙司令员的肯定,并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。
在陈明义等率领下,筑路部队凭着铁锤、钢钎、镐、锹等工具,以“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”和“让高山低头,叫河水让路”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,依靠集体智慧,同大自然进行顽强搏斗,大战雀儿山,突破怒江天险,劈开燃乌沟石峡,奋战波密泥石流等,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壮歌。官兵们豪迈地说:“山再高,没有我们的意志高;石再硬,没有我们的骨头硬。”在许多险峻的工段上,指战员克服高山缺氧,呼吸急促,心跳加速的困难,在数十米乃至上百米高的悬崖上硬是炸出一段段公路;高原厚厚的冻土层,使用镐、锹等工具,只能砸出一个个白印,官兵们便到几里甚至十几里外砍柴,放在冻土上用火烧,烧化一层挖一层;面对巨大的塌方、泥石流和洪水,大家英勇无畏,百折不挠,一面掩埋遇难的战友,一面重新修建被毁坏的公路;在大雪封山的日子,补给不上,只能喝稀饭、吃野菜。由于在高原长期进行强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良,不少人患心脏病、高血压、夜盲症等,腿部浮肿,指甲凹陷,但他们全然不顾,仍顽强战斗在筑路第一线。
看着舍生忘死、英勇奋战的官兵,陈明义既为有这样的部属自豪,又十分心疼。他了解到有的筑路部队在体检中发现10%到15%的同志患了高原心脏病,不少人得了夜盲症等疾病,心急如焚,及时采取措施加强医疗工作,改善生活条件,派人到内地购买维生素C、鱼肝油和高蛋白食品等,给战士们补充营养,并有计划地安排部队在冬季休整。到1953年春季,经过冬季不间断的轮休,官兵们患病的情况已得到改善。
1954年3月,公路修到波密地区,离拉萨已不太远。部队在帕隆藏布江边摆开了筑路战场,当时正值春天,天气好,施工地域海拔又低,官兵们干劲十足,到4月下旬大多数路段已开出路基,有的已开始铺设路面。但这一年雨季来得早,雨量又特别大,江水猛涨。随着气温升高,线路上最大的冰川大规模融化,汹涌的泥石流和洪水,冲毁和淹没了刚建好的31.5公里路基,沿江修建的挡土墙和桥涵被一扫而光,即将竣工的通麦大桥被冲垮,官兵牺牲58人。一时间埋怨情绪纷起,不少同志认为设计线路离江岸太近,勘测技术人员也觉得有口难辩。陈明义及时召开修建司令部会议,明确指出:施工地区千百年无人烟无资料记载,我们对冰川、泥石流、洪水、地质、地形等自然情况认识不足。再加上任务紧迫,降低了路基线位,结果欲速则不达。这次水毁工程,责任在领导,由我们承担。要深刻吸取教训,振奋精神,更加努力,确保年底通车拉萨。陈明义主动承担责任,关心和爱护技术人员,使大家深为感动。会后,陈明义跑遍了水毁地段,与工程技术人员和官兵们认真研究改线和应对冰川、泥石流等的方案。部队再次斗志昂扬地投入到施工中荣耀配资,奋力把被洪水吞噬的宝贵时间抢回来。帕隆藏布江终于让路了,公路向西延伸。
1954年12月,在陈明义等率领下,筑路军民胜利完成了康藏公路修建任务。为此,有约3000名军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建设这条公路,国家共投入资金2.06亿元,全线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多万立方米,架设桥梁430多座,打通涵洞3800多条。不少公路专家感慨地说:这创造了中国筑路史上“最高、最险、最长、工程量最大、建设速度最快五大奇迹”。

修建西藏第一座机场——当雄机场
康藏公路通车后,陈明义担任过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,司令员,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,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旧中国的西藏没有航空事业。抗日战争时期迁居重庆的国民党政府,为了军事的需要,曾委托中国航空公司开辟经川(成都)、康(康定)、藏(拉萨)然后飞往南亚国家的国际航线,因巍巍高原的险峻阻隔而未成功。
和平解放后的西藏,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发展较快,迫切需要开辟从西藏到内地的空中运输线。1956年初,中央决定在拉萨附近修建一座机场,以供民航和空军使用,旋即成立了以陈明义为指挥长的工程建设指挥部。
西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,气候恶劣,雷雨、冰雹、风沙和高空强气流带肆虐,曾被世界航空界视为空中禁区。修建机场的技术标准,不仅国内无先例可循,就连苏联也没有类似经验可参照。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曾向苏联专家请教,得到的回复是:苏联没有这样的高原机场,飞机设计时也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。由于西藏海拔高,空气稀薄,机场跑道需要比内地机场的更长,才能保障飞机的安全起降。为精确计算出飞机的安全起降距离,空军请了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反复计算、验证,测算出需要修建一条4000多米的跑道。这一结论为机场选址和建设打下了理论基础。
陈明义带领军区测绘队会同空军派出的勘察组,先后在拉萨、曲水、羊八井、当雄、日喀则、黑河等地踏勘,预选了6个场址。其中距离拉萨市约180公里的当雄县城西南的一片草地,地势平坦,地质条件和净空较好,不占群众草场、耕地。经报请国务院和解放军总参谋部同意,确定作为机场场址。施工部队由兰州军区空军工程技术人员、工程兵建筑102团和西藏军区工兵团、重型机械营、157团等1万余名指战员组成,又从西藏各地组织民工6000余人加入修建队伍。
1956年3月下旬,陈明义带领有关人员前往当雄。当时,他正患感冒发高烧,这在高原地区极容易引起肺水肿、脑水肿等病变。由于任务紧迫,陈明义不顾医生劝阻登车出发。3月的高原仍天寒地冻,他在吉普车上受凉,感到头痛加剧,四肢乏力,只好在途中住下来,搭起小帐篷宿营。经打针服药后,第二天体温有所下降,即匆匆向当雄赶去。
地处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麓的当雄,平均海拔4200多米,地势较平坦,为高原牧区,平均气温较低,冬春常下雪。陈明义和指挥部有关人员踏着斑驳的雪迹,迎着刺骨的寒风,走遍了预定修建机场的地段,仔细察看各处地质地貌。原设计的跑道的东北端有一小山岗,必须削高垫低,为此将挖填土方55.5万立方米。陈明义凭着几年筑路施工的经验,提出把跑道改向东南方向延伸,可大大减少对小土岗的挖土量,节约大量工时。指挥部组织技术人员对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作了反复研究论证后,上报总参谋部得到批准。此举减少挖填土48万立方米,少用了80万个劳动日,为提前建成机场提供了保证。
工程建设中,陈明义把指挥部设立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地上,一直奔忙在施工一线。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,国家经济比较困难,部队的机械设备不多。汉藏军民用简陋的铁锹等工具,在草原上一遍又一遍地平整土地。由于水泥等匮乏,无法修建混凝土跑道,只能用普通石质材料代替,用沥青铺设。碾压机少,就用石磙子压实跑道。为充分发挥数量不多的机器设备的作用,机械推土和沥青铺设均是昼夜轮班作业,机械的轰鸣声在草原回荡,熬制沥青的火焰映红夜空,展示了汉藏军民改天换地的决心和力量。
1956年4月中旬,陈毅元帅率领中央代表团由西宁乘汽车,经12天艰苦行程来到拉萨,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。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向陈明义提出,能否加快机场施工进度,让陈毅元帅和中央代表团乘飞机回北京。陈毅在藏时间只有40天左右,必须在这期间把机场跑道修好。陈明义与工程技术人员认真讨论研究后,决定先修一条3000多米的简易跑道,待陈毅等飞回北京后,再按原计划修建正式跑道。在他的率领下,军民苦战28天,一条简易跑道终于建成,奇迹般地出现在古老的唐古拉山下。经空军工程技术人员测试鉴定,简易跑道符合飞机安全起降的标准。
与此同时,空13师副师长韩琳等打破空中禁区,试飞青海玉树至当雄成功。1956年5月31日,3架伊尔-12飞机平稳地停靠在机场跑道上。机场上的汉藏军民载歌载舞,一片欢腾。陈毅元帅在张经武、张国华等陪同下,与中央代表团的同志一起来到机场。陈老总看见新建的机场和停泊的飞机,高兴地对陈明义说:我来西藏坐了10多天汽车,万万没有想到,短短几十天里,你们在藏北草原修建了新机场。我和代表团的同志能坐飞机回北京,真是奇迹,真是人生一大幸事。陈明义同志,我们要感谢你的当雄机场啊!是你们让西藏腾飞起来啦!陈毅元帅健步登上飞机,成为第一批由西藏高原飞往内地的乘客。
当雄机场于1956年9月5日全部建成,总计用工36.5万个,铲除土方43万立方米,用沥青1.58万吨,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经费。这是西藏的第一座机场,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,第一座在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试飞成功的机场。机场建成后,经多次试航,开通了北京—成都—拉萨航线,开创了西藏航空事业。

修建西藏第一条国际公路——中尼公路
1961年10月15日,我国政府与尼泊尔王国政府签订了修筑中尼公路的协定。这是第一条从西藏通向境外的国际公路。双方组成了中尼公路建设领导小组,中方组长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。为具体组织公路修筑,成立了工程指挥部。对于谁来担任这支筑路大军的指挥官,周恩来总理一锤定音:请陈明义再给西藏人民修一条走出国境、走向世界的公路。
中尼公路北起当雄县的羊八井,经日喀则、拉孜、定日、聂拉木,再由樟木口岸过友谊桥进入尼泊尔王国,终点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,全长900余公里。中国境内段为800余公里,其中新修路线约500公里。尼泊尔路段友谊桥至加德满都,长约110公里。
1962年春,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义,作为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兼党委书记,同铁道兵副司令员兰庭辉、国家交通部办公厅主任李浩然等一道,率勘测人员等一行20余人,由拉萨出发,对公路进行勘察、测量、定线。他们乘车出定日河谷以后,换乘马前进。在翻越5000多米的朗弄拉和业里雄拉山时,天寒地冻,有的地方积雪一米多深,即下马艰难步行。从聂拉木往下一段,海拔陡降,深山峡谷,悬崖峭壁,下山要拽着路边小树或拉着绳子,才能挪动脚步。陈明义等亲临实地考察,取得大量数据和第一手资料。经反复研究,形成了公路修建方案,上报国务院后很快得到批准。6月,在陈明义率领下,由铁道兵、工程兵、工兵、步兵、藏族民工队和四川等地调来的桥工队组成的万人筑路大军,开始了在喜马拉雅高山峡谷开拓筑路的英雄壮举。
新建线路中从定日到友谊桥工程最为艰巨,要经过6座大山和无数道激流,从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之间,横跨喜马拉雅山脉的分水岭,然后盘旋直下到达中尼边境,施工条件差异性大。北段线路,在喜马拉雅山区,冰峰雪岭林立,空气稀薄,风沙很大,天气恶劣多变,昼夜温差有时达20多摄氏度。南段线路,海拔急剧下降,聂拉木到友谊桥直线距离不足20公里,海拔下降竟达2000多米,有20多段线路要从三四百米高的绝壁悬崖上通过。一些当年的建设者回忆:在这种地段上施工,从悬崖上挂一根保险绳都要付出极大的勇气、智慧和劳动。战士们必须在悬空摇荡的条件下打炮眼,多次爆破才能开出一个小小的立足点,然后从这点出发逐步展开作业,凿通石壁。有的驻地和工地近在咫尺,但上工和下工都要经过吊绳、软梯、独木桥等多种地段,攀行长达一两个小时。
在那段日子里,陈明义终日奔波在工地上,对每一项重点工程,现场议事,现场决定,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有一段时间,石方工程非常集中,不少单位进度缓慢。陈明义等及时组织开展工程民主,进行技术革新。官兵们群策群力,采取深打炮眼和放排炮、葫芦炮、缝子炮等办法,大大提高了工效。铁道兵24团开凿一段绝壁时,挑选18名官兵组成突击队。他们身系保险绳,在半空中作业,苦战一个半月,用排炮和葫芦炮将半截石壁掀入深谷,每工日平均完成28.8立方米,达到国家定额的14.76倍。某部班长张相如冒险钻进石壁的天然裂缝里,选择合适位置实施爆破,仅用3包炸药就炸下3000多立方米岩石。在公路建设的3年中,共推广运用先进经验400多条,采取合理化建议上千条。
陈明义特别重视对筑路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,要求官兵严守边防有关规定,关心爱护中尼边民利益。在樟木村附近施工时,为保护群众的4亩耕地和当地仅有的一棵梨树,部队想尽办法,增添2200立方米的砌石工程,多用3000个工日,樟木村群众无不感动。一个尼泊尔孩子误入爆破区,在临爆的一瞬间,一名战士从防炮洞跳出去,用身体掩护了孩子。类似的事例数不胜数,在中尼边境传为佳话。
1962年10月,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。陈明义奉命上前线,负责战时后勤保障的统一指挥,中尼公路工程指挥长改由西藏军区副参谋长陈子植担任。战后,陈明义继续担任中尼公路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一职,对修建中的重大问题决策把关。在陈明义、陈子植等带领下,筑路军民经过3年艰苦奋战,于1965年胜利完成国内段的修筑任务。这期间,应尼泊尔王国政府请求并经国务院批准,陈明义还亲自组建了一支500多人的援尼工程大队,帮助建设尼境内公路及辅助设施。中尼公路于1967年5月26日全线通车,谱写了一曲中尼人民友谊之歌。
为此,有109名官兵献出宝贵生命,其中87人安葬于聂拉木县樟木烈士陵园。工程指挥部撰写的烈士公墓碑文上,镌刻着筑路官兵的英勇事迹:“万众一心,劈开世界高山,群策群力,斩断激流险江。轻度索桥,灵活机智,飞攀软梯,英勇顽强。藏族人民,奔走欢唱,踊跃支前修路,热情建设家乡。辛劳三载,筑路千里。万古险阻变通途,传统友谊增异卉。舍己为公,一心向党,烈士捐躯,山河气壮。精神永垂不朽,品质闪耀光芒。”在之后的岁月里,陈明义每次到樟木边防前哨视察,都要走进烈士陵园,看望长眠的战友,肃立默哀致敬。
修建西藏第一座现代航空港——贡嘎机场
民主改革后的西藏,经济社会快速发展,大大增加了对航空运输的需求。当时我国已引进苏联伊尔-18飞机,当雄机场的净空、跑道等显然不适应大型飞机起降的需要,且海拔高,离拉萨也较远。20世纪60年代中期,国家决定在拉萨附近重新选址,建设一座现代化机场。为此,西藏自治区和西藏军区共同组建机场修建委员会,由陈明义任主任并兼任工程指挥部指挥长,西藏自治区工委副书记杨东生、西藏军区副参谋长李克林任副主任。
陈明义和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高厚良率工程技术人员,在方圆几百里的拉萨四周勘探测量,选了三个机场地址。第一个在拉萨东郊蔡公塘。这里离拉萨不远,交通方便。但是,净空不够,还要占用老百姓的良田,且与拉萨的距离过近,将影响拉萨的长远建设。这个方案,被陈明义坚决地否定了。第二个是扎朗。这里离拉萨110公里,净空也好。然而,陈明义考虑到扎朗是山南的粮仓,耕地质量好而少,不能把山南粮仓的良田占了。第三个是贡嘎。该地离拉萨90公里,乘汽车1个小时可到达。这里的贡嘎河河滩宽广,地质条件好,重点是跑道建在河滩上,占用群众的耕地少。陈明义与空军领导及专业人员,认真研究有关技术资料,分析各点的优势。经反复对比、论证、研究,拟定把新机场修建在贡嘎。1966年1月,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批准在贡嘎修建现代化机场。
是年3月,机场建设全面展开。这是一座设备完善的高质量的现代化航空港。当雄机场的跑道是柏油浇铺的,贡嘎机场跑道全部用水泥浇筑。跑道长3500米,两头还建有500米的保险道,以保证伊尔-18等飞机安全起降。陈明义在开工动员大会上强调指出:这是西藏第一座现代化机场,离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近,既可民用又可军用。把机场修好,在政治、经济、国防和外交、旅游等方面都有重大意义,必须坚持百年大计,质量第一。
机场除修建高质量规范的跑道外,还要修筑一系列配套工程:候机大厅、指挥塔、气象台、调配指挥中心、机场场部大楼、警卫部队营房、空勤招待所等,并为当日不能返回的飞机,修建能停放10架以上的停机坪房。
担负机场施工任务的主要力量,是铁道兵、西藏军区工兵部队和空军工程技术人员等约8000人,另动员数千名汉藏民工配合。这几支部队善于在艰苦条件下打硬仗,但承建高标准大型现代化机场还是首次。陈明义严格要求他们一切按照施工规范操作。同时规定,工程技术人员加强指导监督,所有技术标准都必须严抓细抠,一一落实,确保工程质量优良,万无一失。开工不久,西藏同全国一样陷入“文革”旋涡中,有人提出:“我们是不是也要搞运动?”施工队伍出现情绪波动。陈明义果断地下达命令:“我们这里要集中精力搞国防建设,搞现代化机场的修建,不准搞这个那个的。”他及时排除了干扰,机场修建始终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。为保证部队稳定和施工质量,他亲自在工地坐镇,掌握具体情况,处置突发问题。为维护群众利益,少占或不占耕地,减少纠纷,陈明义下令机场用地尽量往河滩挪移,在河边加修一道道坚固的堡坎、河堤等保护工程,以确保机场质量。
年底,机场修建提前竣工,工程质量和建设速度,当时在国内堪称一流。11月23日,民航拉萨站从当雄机场转场至拉萨贡嘎机场。1967年2月,陈明义奉命去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。此时,经过装配、调试设施设备和飞行试航,贡嘎机场已可以起降飞机。他乘坐从机场起飞的第一架伊尔-18客机飞向北京。陈明义透过明亮的机窗向下俯望,昔日野草遍地的河滩已变成了一座现代化航空港。陈明义作为西藏历史巨变的亲历者和见证人,不禁感慨万千,深感自豪。
陈明义在西藏工作期间,不仅指挥修建了康藏、中尼公路和当雄、贡嘎机场,还在西藏军区司令员任上领导建设了日喀则和平机场、昌都邦达机场等。他不愧为“西藏现代交通事业的开拓者”。
1975年秋,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军区司令员的陈明义,告别了战斗了25年的西藏高原,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。这位当年满头青丝的年轻将军,此时两鬓染霜已近花甲之年。1986年陈明义离职休养后,仍心系西藏边防和西藏的建设发展。
2002年5月,陈明义因病去世,享年85岁。
本文为《党史博览》原创
未经许可不得转载、摘编等。侵权必究。
热丰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